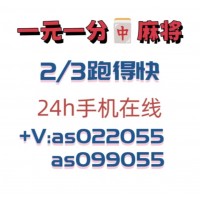人生谢世即是读不完的实际作品,由于生存从来创造着实质故事。 广场边上一个偶尔玫瑰摊位前,围着七八部分,在等着买玫瑰。卖玫瑰的小伙子,刻意地修剪包装,当他笑着递给主顾时,那笑脸,不知干什么熏染了小雪。 胆大的,干脆一不住,二不休,一改就是七、八岁,甚至上十岁。这样一改,有兄弟姊妹的,便出现哥哥小于弟妹的了。 这一说我就明白了。只是,把官场的改年龄,与改革扯到一起,似乎有些牵强。对我的看法,朋友却不以为然。朋友反问我,那你说什么才叫改革呢?当是有人认为,现在实行的游戏规则,对发展或某些人的利益不利,尝试着去改变。任何改革的背后,其实都是利益二字。从商鞅、王安石,到戊戌七君子,改革,哪个不是利益调整。有大权的调整大利益,小权的调整小利益,原理都是一样的。掌握大权的人,笑掌握小权的人,为了一些也许在他们看来的蝇头小利,干些小改小革的事,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。 朋友说,就说这改年龄吧,虽然我也不赞成,但是我也理解。你想,一些人在领导岗位干了多年,除了当官,别无它长,既不能做工经商,种田打工,也不能像你们一样,可以上网写文章。官,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全部价值体现。在位的时候,他们掌握住许多社会资源,可以支配。经常差三遣四,呼风唤雨惯了,突然叫他下来,适应吗?别要笑他们觉悟低,小见,其实,只有永远的利益,没有永远的觉悟。《劳动法》明明规定,男60岁,女55岁退休,没有规定谁是法律之外的特殊公民。可是,权大位高的,就可以干到70岁,甚至更大。既然权大的可以改变法律,权小的为啥不可以改改年龄? 我明白了,利益决定改革的取向和态度。但是,明白归明白。并不是一切明白了的事情,就可以坦坦荡荡,心安理得,明明白白地去做的;尤其是改革,这个玩利益魔方的游戏,往往暗藏着许多难以捉摸的玄机与危险。君不见,商鞅气势如虹,开阡陌封疆,废除井田制,着实为新兴的地主和自耕农谋了一把利益。可是,当保守势力复辟时,这一切功绩都是以车裂作结。倚仗着光绪帝气息奄奄的圣威,戊戌七君子雄心勃勃,在百日维新中,几乎每天都要颁布一条变法诏令。可是,慈禧太后一政变,这些诏令几乎就成了一纸空文,七君子的头颅,则成了变法祭坛上的祭品。翻开历史,改革者的旗帜,似乎都写满了血祭二字;改革,本身就是一部不堪回首的沉重历史。 当然,流血也罢,断头也罢,改革照样在进行。这既是利益重整的需要,也是社会进步的要求。就像女人的分娩,明明知道要流血,要疼痛,仍有一代又一代的人,在这条血与痛的路上接踵而行。不难设想,如果从混沌初开的那天起,这世界就没有改革,完整地保持着原来的样子,我们现在的生活将会是怎样。我们应当还居住在山洞或树上,天天含毛茹血,撕食着生的鱼或猎物;结绳记事,钻石取火,徒步当车,是我们日常的生活交往方式;我们仍循规蹈矩,在孔孟之道的伦理纲常下,维系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关系。不敢再往下想了。我理解了改革,理解了那些产妇们,她们的伟大,她们的献身精神。为什么明明看见有人在产床上痛苦挣扎,仍不断有人从容走进。 产妇是伟大的,母亲是伟大的,改革是伟大的。现在,坚持天不变,道也不变,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人,也很难找了;相反,改革成了一个很褒义,很开明,很进步,很时髦的词。坊间有说法,改革是个筐,什么都可往里装。为什么要装?因为这一装,不仅装进去了一种褒义,开明,进步和时髦,还装进了掌权者的心事和期望。何况,现在再也没有了商鞅车裂和七君子那样断头的风险。据一位江苏来的朋友讲,他们市里最近在8名县处级干部任用上,进行了一项众口难调的改革。改革的主要内容是“三个突破”:一是突破选拔方式。由过去的组织考察任用,为面向社会公开选拔。二是突破年龄。由过去的45周岁以下,放宽到50周岁。三是突破身份。不局限于公务员,不是公务员的,中选后可依法转变身份。 倡导这项改革的领导,讲了许多这次改革意义深远。大概意思是,这是创造性地贯彻党的干部路线的需要;是充分发扬民主,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大胆创新;是重规则,身份,年龄,又不唯规则,身份,年龄的具体体现。许多人曾深深感动,为领导的胆识和魄力;特别是一些在传统规则之外,对升迁已失去信心的人。他们仿佛在漫漫长夜行走,满眼迷惘,不知方向,突然发现一颗耀眼的启明星,从东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。 报名,资格审查,笔试,面试,考察,通过,公示,任用,一切似乎都在合情合理,规范有序地进行。然而,当最后的结果揭晓,人们似乎才明白了什么。原来,在改革中脱颖而出的,大都是几个主要领导的老俵舅子亲信朋友。如果按照正常的规则,他们实在没有合法的理由,跨入这道高高的门槛;改革,却给他们搭建了一架登天的云梯,合乎逻辑地,堂堂皇皇地。情况被反映了上去,上边派来了调查组。调查的结论是,这次的公开选拔,确有不完善之处。但改革中的问题,只有在改革中解决。在没有新的、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举措之前,此项改革暂缓再进行。 也有人说,那向上反映情况的信,其实也是领导暗示亲信写的。原因很简单,改革就允许探索,允许不完善。只要没有真凭实据营私舞弊,谁会处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领导该办的事,已在改革中完成。领导也没有心思,让这个撕开的口子永远张起,真的要破格提拔那些与己无关的人。 ,3点,还是四点,恍惚中,我没太听清。但它发出的声音,与三十多年前一样干净。清脆的钟声,使我想到钟里面悬挂的,一只小小的白色鸽子――我幼年时期的唯一证据。它红色的圆眼睛,见识了曾经的时光岁月,它一如当初的保持了原生模样,而我浓密的发丝,正一天天的不幸被什么连根拔掉―――拥有这只小鸽子时候,我仅仅几岁年纪。父亲交给我怎样吹,拿捏的姿势,运气的方法。我须承认,那时父亲的脖颈,是我行路的车辇。但是后来,我和父亲之间,矛盾究竟始与何时?接近凌晨,我仍被这个问题搅得不能安眠,朦胧着努力搜寻相关的信息。这个时候,熟睡中的父亲突然叫喊起来,一声接一声叫的骇人。我吓了一跳,翻身坐起。妈也醒过来,推搡父亲,说,你醒醒,醒醒,又喊梦话了。父亲哼了一声,清醒了,再没说什么。 一切又沉默下来,妈这次再没有睡。她点着一颗纸烟,一点火亮忽闪的明明暗暗。妈的心思,便也跟烟光一样,我知道妈的性格。去年春节,她也是这个样子。日期不是隔的很远,因此我记得准确时间―――腊月二十八那天。我和两个表弟开车,从县城赶回乡下,接妈和父亲来城里过年。之前老早就跟妈说过,妈非常高兴。我担心父亲,妈说不用担心,你爹那边我去说。后来妈在电话里告诉我,父亲也同意了。我想,父亲难得这么痛快的答允,许是他自己寻思开了,也可能是在妈的劝解下。不管怎么样,他答允了就好。 中午,我和表弟赶到家,妈已经收拾好在等。妈叫父亲换衣服,父亲不换,坐在炕沿抽烟。妈催促,他的脸色越发难看了。我知道父亲上来拗脾气,不解地用眼神询问妈。表弟见状,抢下父亲的烟,扯他胳膊,嘴里不停劝慰。父亲却像是下了决心,一动不动。僵持一阵,父亲突然掉了泪,孩子似的抽泣,继而嚎啕。妈恨恨地数落他,孩子好心来接,你不领情算了!你不去,我一个人去!父亲借机和妈吵,声音高的简直是咆哮了。幸亏两个表弟,耐心劝,才不太情愿地上了车。 03年春节我过的非常懊悔。懊悔不该接父亲进城,伤害了一大家子人,伤了我的面子。我说不清与父亲的隔阂诞生何时,但可以肯定,父亲不断孳生风波,一切细微迹象让我对他的恼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三十晚上,哥聚拢全家人一起辞旧迎新。因为父亲的在场,年夜饭吃的人人郁郁寡欢。嫂子请他做上首位置,他再三推辞。侄女给他夹菜,小盘子里的食物堆成山,也不投入一箸。哥为他倒酒,他捂住酒杯,眼皮也不抬说头疼。哥殷勤地说,白酒不喝喝啤酒吧。这下,他干脆把酒杯一趸,坐在那里。哥说,象征性喝点,过年喜庆,咱喝红酒。我明白,哥的话含有隐意,父亲绝不会听不除弦外之音。我想父亲懂了,一系列行径就能适当收敛。但无论怎么做,父亲也极少言语,不露笑容,仿佛脸上的皱纹冻结,和茫茫冰雪一样。 大家小心翼翼,观察他的表情和神态。生怕哪句话说错,惹恼了他。面对丰盛的菜肴,谁也无意吃。我心里悔的不行,责怪自己,也怪罪父亲不识恭敬。大家尊重他,觉得他既然是我的父亲,也相当与他们的父亲。可是父亲故意悖理,天知道他想的什么!蜻蜓点水似的,父亲胡乱咽下几口菜,起身离桌。站起的时候,他一手扶了膝盖,一手摸着后腰,稍稍趔趄一下,再站稳,抽身。我快速溜他一眼,继续吃饭。那时,他在于我,已经是陌生人了。 初二大早,父亲不顾众人挽留,叫妈跟她回家。我看得出,妈不乐意走。但父亲坚持走,妈必须跟从他。我穿了棉衣要送送妈,妈拦挡不让,妈说外边冷,小心冻感冒。我含着眼泪,往她衣兜里塞钱。妈硬生生拽我的手,我不甘心,又往里塞。几张纸币揉搓成一团。父亲在一旁看着,默不作声。有一瞬,他刚好和我对视了,又迅速移开。我想,他那时必是十分愧疚的。而他不说出来,也没有更改自己的意思。望着他在楼下越行越远的背影,我在心里狠狠地诅咒他,甚至盼他死掉。我说,你不是我父亲。不是我父亲。不是!我这样说的时候,泪流满面。 待我被灶膛里柴禾燃烧的噼啪声惊觉,才知自己困顿之极睡着了。天早已大亮,妈在厨房忙着烧水,煮饭。屋中有一些炝人的青烟味,妈拉开风扇,满屋子便是蜜蜂飞翔般的旋转声。隔夜的剩菜,在炉子上的小铁锅里加热,此时吱吱作响。看下时间,我在一屋子的菜香中起床,上厕所,洗漱。接着妈说,饭好了,吃饭吧。妈掀开锅盖,蒸腾的热气即刻弥漫。妈一样一样往桌上端菜,头发上凝结一层水珠。我呆呆的看着眼前的情景,蓦地,似乎一下子时光倒流几十年。不知不觉,眼泪又涌上来。我说妈一起吃吧。妈说,你先吃,吃完赶早车回家看看。我没答话,我心里的确这么想。孩子的心思,当妈的总是猜的准。 吃饭时候,我猛然想起父亲。便问道,爹呢?妈进了里屋,撩起围裙抹揩双手,打听车去了。初一,怕是人家不通车呢。你爹说也许能通,去问问好。我哦了一声。妈看着我,欲言又止的样子。 没过几天,头儿说,要把小饭馆的服务人员清理一下。我接受命令,跑去找老板,询问了一些事情。开始,老板言辞闪烁,语焉不详。我说这事开不得玩笑,弄不好你的饭馆也要关门。老板这才告诉我,刘红梅的事情确实有这样的事情,但作为老板,又在单位的地皮内,他不敢轻易得罪人,怕跟自己惹麻烦,这我能够谅解。但还得履行指职责,让他劝刘红梅离开单位,到他处务工去吧。老板说这样最好,叫来刘红梅,说了我的意见,我也对她说,这里已经不适合你待了,到别处说不定更好。
人生谢世即是读不完的实际作品,由于生存从来创造着实质故事。 广场边上一个偶尔玫瑰摊位前,围着七八部分,在等着买玫瑰。卖玫瑰的小伙子,刻意地修剪包装,当他笑着递给主顾时,那笑脸,不知干什么熏染了小雪。 胆大的,干脆一不住,二不休,一改就是七、八岁,甚至上十岁。这样一改,有兄弟姊妹的,便出现哥哥小于弟妹的了。 这一说我就明白了。只是,把官场的改年龄,与改革扯到一起,似乎有些牵强。对我的看法,朋友却不以为然。朋友反问我,那你说什么才叫改革呢?当是有人认为,现在实行的游戏规则,对发展或某些人的利益不利,尝试着去改变。任何改革的背后,其实都是利益二字。从商鞅、王安石,到戊戌七君子,改革,哪个不是利益调整。有大权的调整大利益,小权的调整小利益,原理都是一样的。掌握大权的人,笑掌握小权的人,为了一些也许在他们看来的蝇头小利,干些小改小革的事,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。 朋友说,就说这改年龄吧,虽然我也不赞成,但是我也理解。你想,一些人在领导岗位干了多年,除了当官,别无它长,既不能做工经商,种田打工,也不能像你们一样,可以上网写文章。官,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全部价值体现。在位的时候,他们掌握住许多社会资源,可以支配。经常差三遣四,呼风唤雨惯了,突然叫他下来,适应吗?别要笑他们觉悟低,小见,其实,只有永远的利益,没有永远的觉悟。《劳动法》明明规定,男60岁,女55岁退休,没有规定谁是法律之外的特殊公民。可是,权大位高的,就可以干到70岁,甚至更大。既然权大的可以改变法律,权小的为啥不可以改改年龄? 我明白了,利益决定改革的取向和态度。但是,明白归明白。并不是一切明白了的事情,就可以坦坦荡荡,心安理得,明明白白地去做的;尤其是改革,这个玩利益魔方的游戏,往往暗藏着许多难以捉摸的玄机与危险。君不见,商鞅气势如虹,开阡陌封疆,废除井田制,着实为新兴的地主和自耕农谋了一把利益。可是,当保守势力复辟时,这一切功绩都是以车裂作结。倚仗着光绪帝气息奄奄的圣威,戊戌七君子雄心勃勃,在百日维新中,几乎每天都要颁布一条变法诏令。可是,慈禧太后一政变,这些诏令几乎就成了一纸空文,七君子的头颅,则成了变法祭坛上的祭品。翻开历史,改革者的旗帜,似乎都写满了血祭二字;改革,本身就是一部不堪回首的沉重历史。 当然,流血也罢,断头也罢,改革照样在进行。这既是利益重整的需要,也是社会进步的要求。就像女人的分娩,明明知道要流血,要疼痛,仍有一代又一代的人,在这条血与痛的路上接踵而行。不难设想,如果从混沌初开的那天起,这世界就没有改革,完整地保持着原来的样子,我们现在的生活将会是怎样。我们应当还居住在山洞或树上,天天含毛茹血,撕食着生的鱼或猎物;结绳记事,钻石取火,徒步当车,是我们日常的生活交往方式;我们仍循规蹈矩,在孔孟之道的伦理纲常下,维系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关系。不敢再往下想了。我理解了改革,理解了那些产妇们,她们的伟大,她们的献身精神。为什么明明看见有人在产床上痛苦挣扎,仍不断有人从容走进。 产妇是伟大的,母亲是伟大的,改革是伟大的。现在,坚持天不变,道也不变,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人,也很难找了;相反,改革成了一个很褒义,很开明,很进步,很时髦的词。坊间有说法,改革是个筐,什么都可往里装。为什么要装?因为这一装,不仅装进去了一种褒义,开明,进步和时髦,还装进了掌权者的心事和期望。何况,现在再也没有了商鞅车裂和七君子那样断头的风险。据一位江苏来的朋友讲,他们市里最近在8名县处级干部任用上,进行了一项众口难调的改革。改革的主要内容是“三个突破”:一是突破选拔方式。由过去的组织考察任用,为面向社会公开选拔。二是突破年龄。由过去的45周岁以下,放宽到50周岁。三是突破身份。不局限于公务员,不是公务员的,中选后可依法转变身份。 倡导这项改革的领导,讲了许多这次改革意义深远。大概意思是,这是创造性地贯彻党的干部路线的需要;是充分发扬民主,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大胆创新;是重规则,身份,年龄,又不唯规则,身份,年龄的具体体现。许多人曾深深感动,为领导的胆识和魄力;特别是一些在传统规则之外,对升迁已失去信心的人。他们仿佛在漫漫长夜行走,满眼迷惘,不知方向,突然发现一颗耀眼的启明星,从东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。 报名,资格审查,笔试,面试,考察,通过,公示,任用,一切似乎都在合情合理,规范有序地进行。然而,当最后的结果揭晓,人们似乎才明白了什么。原来,在改革中脱颖而出的,大都是几个主要领导的老俵舅子亲信朋友。如果按照正常的规则,他们实在没有合法的理由,跨入这道高高的门槛;改革,却给他们搭建了一架登天的云梯,合乎逻辑地,堂堂皇皇地。情况被反映了上去,上边派来了调查组。调查的结论是,这次的公开选拔,确有不完善之处。但改革中的问题,只有在改革中解决。在没有新的、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举措之前,此项改革暂缓再进行。 也有人说,那向上反映情况的信,其实也是领导暗示亲信写的。原因很简单,改革就允许探索,允许不完善。只要没有真凭实据营私舞弊,谁会处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领导该办的事,已在改革中完成。领导也没有心思,让这个撕开的口子永远张起,真的要破格提拔那些与己无关的人。 ,3点,还是四点,恍惚中,我没太听清。但它发出的声音,与三十多年前一样干净。清脆的钟声,使我想到钟里面悬挂的,一只小小的白色鸽子――我幼年时期的唯一证据。它红色的圆眼睛,见识了曾经的时光岁月,它一如当初的保持了原生模样,而我浓密的发丝,正一天天的不幸被什么连根拔掉―――拥有这只小鸽子时候,我仅仅几岁年纪。父亲交给我怎样吹,拿捏的姿势,运气的方法。我须承认,那时父亲的脖颈,是我行路的车辇。但是后来,我和父亲之间,矛盾究竟始与何时?接近凌晨,我仍被这个问题搅得不能安眠,朦胧着努力搜寻相关的信息。这个时候,熟睡中的父亲突然叫喊起来,一声接一声叫的骇人。我吓了一跳,翻身坐起。妈也醒过来,推搡父亲,说,你醒醒,醒醒,又喊梦话了。父亲哼了一声,清醒了,再没说什么。 一切又沉默下来,妈这次再没有睡。她点着一颗纸烟,一点火亮忽闪的明明暗暗。妈的心思,便也跟烟光一样,我知道妈的性格。去年春节,她也是这个样子。日期不是隔的很远,因此我记得准确时间―――腊月二十八那天。我和两个表弟开车,从县城赶回乡下,接妈和父亲来城里过年。之前老早就跟妈说过,妈非常高兴。我担心父亲,妈说不用担心,你爹那边我去说。后来妈在电话里告诉我,父亲也同意了。我想,父亲难得这么痛快的答允,许是他自己寻思开了,也可能是在妈的劝解下。不管怎么样,他答允了就好。 中午,我和表弟赶到家,妈已经收拾好在等。妈叫父亲换衣服,父亲不换,坐在炕沿抽烟。妈催促,他的脸色越发难看了。我知道父亲上来拗脾气,不解地用眼神询问妈。表弟见状,抢下父亲的烟,扯他胳膊,嘴里不停劝慰。父亲却像是下了决心,一动不动。僵持一阵,父亲突然掉了泪,孩子似的抽泣,继而嚎啕。妈恨恨地数落他,孩子好心来接,你不领情算了!你不去,我一个人去!父亲借机和妈吵,声音高的简直是咆哮了。幸亏两个表弟,耐心劝,才不太情愿地上了车。 03年春节我过的非常懊悔。懊悔不该接父亲进城,伤害了一大家子人,伤了我的面子。我说不清与父亲的隔阂诞生何时,但可以肯定,父亲不断孳生风波,一切细微迹象让我对他的恼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三十晚上,哥聚拢全家人一起辞旧迎新。因为父亲的在场,年夜饭吃的人人郁郁寡欢。嫂子请他做上首位置,他再三推辞。侄女给他夹菜,小盘子里的食物堆成山,也不投入一箸。哥为他倒酒,他捂住酒杯,眼皮也不抬说头疼。哥殷勤地说,白酒不喝喝啤酒吧。这下,他干脆把酒杯一趸,坐在那里。哥说,象征性喝点,过年喜庆,咱喝红酒。我明白,哥的话含有隐意,父亲绝不会听不除弦外之音。我想父亲懂了,一系列行径就能适当收敛。但无论怎么做,父亲也极少言语,不露笑容,仿佛脸上的皱纹冻结,和茫茫冰雪一样。 大家小心翼翼,观察他的表情和神态。生怕哪句话说错,惹恼了他。面对丰盛的菜肴,谁也无意吃。我心里悔的不行,责怪自己,也怪罪父亲不识恭敬。大家尊重他,觉得他既然是我的父亲,也相当与他们的父亲。可是父亲故意悖理,天知道他想的什么!蜻蜓点水似的,父亲胡乱咽下几口菜,起身离桌。站起的时候,他一手扶了膝盖,一手摸着后腰,稍稍趔趄一下,再站稳,抽身。我快速溜他一眼,继续吃饭。那时,他在于我,已经是陌生人了。 初二大早,父亲不顾众人挽留,叫妈跟她回家。我看得出,妈不乐意走。但父亲坚持走,妈必须跟从他。我穿了棉衣要送送妈,妈拦挡不让,妈说外边冷,小心冻感冒。我含着眼泪,往她衣兜里塞钱。妈硬生生拽我的手,我不甘心,又往里塞。几张纸币揉搓成一团。父亲在一旁看着,默不作声。有一瞬,他刚好和我对视了,又迅速移开。我想,他那时必是十分愧疚的。而他不说出来,也没有更改自己的意思。望着他在楼下越行越远的背影,我在心里狠狠地诅咒他,甚至盼他死掉。我说,你不是我父亲。不是我父亲。不是!我这样说的时候,泪流满面。 待我被灶膛里柴禾燃烧的噼啪声惊觉,才知自己困顿之极睡着了。天早已大亮,妈在厨房忙着烧水,煮饭。屋中有一些炝人的青烟味,妈拉开风扇,满屋子便是蜜蜂飞翔般的旋转声。隔夜的剩菜,在炉子上的小铁锅里加热,此时吱吱作响。看下时间,我在一屋子的菜香中起床,上厕所,洗漱。接着妈说,饭好了,吃饭吧。妈掀开锅盖,蒸腾的热气即刻弥漫。妈一样一样往桌上端菜,头发上凝结一层水珠。我呆呆的看着眼前的情景,蓦地,似乎一下子时光倒流几十年。不知不觉,眼泪又涌上来。我说妈一起吃吧。妈说,你先吃,吃完赶早车回家看看。我没答话,我心里的确这么想。孩子的心思,当妈的总是猜的准。 吃饭时候,我猛然想起父亲。便问道,爹呢?妈进了里屋,撩起围裙抹揩双手,打听车去了。初一,怕是人家不通车呢。你爹说也许能通,去问问好。我哦了一声。妈看着我,欲言又止的样子。 没过几天,头儿说,要把小饭馆的服务人员清理一下。我接受命令,跑去找老板,询问了一些事情。开始,老板言辞闪烁,语焉不详。我说这事开不得玩笑,弄不好你的饭馆也要关门。老板这才告诉我,刘红梅的事情确实有这样的事情,但作为老板,又在单位的地皮内,他不敢轻易得罪人,怕跟自己惹麻烦,这我能够谅解。但还得履行指职责,让他劝刘红梅离开单位,到他处务工去吧。老板说这样最好,叫来刘红梅,说了我的意见,我也对她说,这里已经不适合你待了,到别处说不定更好。原文链接:http://www.fangnian.net/chanpin/17578.html,转载和复制请保留此链接。
以上就是关于全面升级红中麻将,跑得快上下分群#但闻全部的内容,关注我们,带您了解更多相关内容。
以上就是关于全面升级红中麻将,跑得快上下分群#但闻全部的内容,关注我们,带您了解更多相关内容。







 [VIP第1年] 指数:1
[VIP第1年] 指数: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