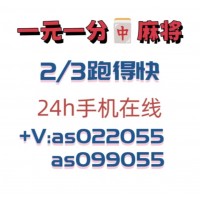以是,爱好款待阳光,携一齐,走向时间的口岸,喝春茶,赏莲花。那些抛弃的过往,逝去的时间,迷惑的情缘,在阳光映照下,重现于宁静的湖面。从来十足都还在原地,花在春天开放,水在夏季澄净,叶在秋天飘落,雪在冬天纷洒。咱们不过一只假冒劳累的蝼蚁,或是强颜欢乐的朵儿,尝尽风尘。或是飘但是过的风,何谈轻重。不是由于淡薄,肤浅和愚笨,不过功夫如风,顾不得那些摩肩擦踵的,顾不得月在更阑的相思。但却忘不了,那月下惦记的密斯。 小时候,身为女儿身的我,却没有一点淑女的气味。那时我性格非常叛逆,总觉的父母、奶奶都不喜欢我,不要我了,把我丢给了姨奶。村里的小伙伴们也同样问我,小丫,你父母呢,我说,在城里上班呢。他们怎么不来看你?我支支吾吾的说,……他们很忙哩,没有空。后来,小伙伴们又问,我还是这样回答,再后来,小伙伴们就半信半疑的了。有一天,我和小菊正在玩石子,王小强过来,一把将我们的石子抢去,我们问他要,他说就不给你,有本事叫你爸妈来拿呀。我说,我爸妈都在城里上班过不来,他说,这么长时间都不见他们来,骗人,你是不是你姨奶捡回来的呀。当时,我被他的话激怒了,伸出手就在他没有防备时的脸上重重的一拳,顿时鲜血便从他嘴角边汩汩的流出来,我被吓坏了,转身向麦场飞快的跑去。王小强的妈在村里是有名的骂街高手,谁都不敢惹她,这回我把她的儿子打的鲜血淋淋,还不知道她怎么骂呢。我不敢回家,躺在麦垛上,想着想着竟不知不觉的睡着了,醒来时候月亮已经悄悄地爬在我的脸上,这时我听见有人在隐隐约约的喊着小丫,快回来,我不打你……。回到家,姨奶真的没打我,而且也没有提王小强他妈的事,我这才安下心,钻到被窝里去。 第二天,小菊来找我玩,她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,对我说,小丫你家里真富,你父母在城里一定挣很多钱吧,要不怎么给你姨奶买个这么亮的金戒指。我迷迷糊糊的听着,没弄明白怎么一回事,这时看到王小强包着白色的绷带向我们家走过来,他说,你爸妈真的在城里工作呀,还给你姨奶买了金戒指,然后,他又对我说中午他娘炖的鸡特别香。中午,我看到姨奶正在喂鸡,数了数正好少了一只又肥又大的红公鸡。 倒是王六儿一语道破:自古有天理倒没有饭吃哩!他占用老娘,使他这几两银子不差甚么。这样解释于男人和自己,心里还是稍稍有些不安的。无论韩道国怎样的不堪,有此语也算说了一句人话,比起王六儿,还是有一份可爱,哪怕王六儿比他牺牲的多得多。 但,好日子不长,只是三年多,纤细微弱的父亲因积劳成疾被病魔夺走了人命。父亲是家园的顶梁柱,是咱们几个儿童独一的依附。父亲走了,却带不走父亲的可惜以及一人的艰难。父亲谢世时,一家人全靠父亲的五、六十元离休金和2、30斤粮飘委屈生存。厥后父亲开起了饭店,咱们的生存才真实的好起来。但父亲一走,那些全没有了。没有了粮飘,没有了报酬,也没有了家里的顶梁柱和主心骨,咱们家又一次徜徉在生存繁重的十字街口。 /> 怀念磨房 文/云中燕 每当樱桃花红遍山野的时候,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忆起老家的那些磨房。 在老家,每相邻两座大山之间就有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,一条条小河养育了一座座磨房,也养育了像泥土一样厚道朴实的父老乡亲。从我家门前流过的那条河,名叫荨麻河。在小河的上、中、下游,大约每隔公把里就有一座磨房,远远望去,这些磨房就好象用青藤随意串连的一朵朵香菇。房顶,一年四季都是粉粉的、白白的,宛如飘落了一层层细密的火灰,更像是凝固了一片片薄薄的清霜。 老家的磨房大多用竹子建盖,只有少数几间是瓦屋面,房子通常是低矮的、简陋的,这很容易让我想起瘦削而又硬朗的爷爷。磨房的四围均为墙壁,地板被踩得光亮,一盘大石磨和漏斗占据了巨大的空间,旁边就只能容下一个小小的火塘。墙壁也较粗糙,很少经过粉刷,许多不太规则的鼠洞分布其中,最爱使人产生联想。地面,一条条裂纹相互交织着,但几乎所有的缝隙都被磨出的飞面填满,看上去,见到的仿佛是一只饱经沧桑而又刚刚涂了雪花膏的手。 孩提时,我经常被爷爷领着去磨面。每年三月,当一树一树的樱桃花争奇斗艳的时候,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!家里装面的箩空了,我们必须在枯水季节来临前,备足当年夏天吃的面。我是爷爷的长孙,磨面这样的美差,爷爷当然让我和他一起去完成。多少次,在逼窄的田埂上,爷爷一手搂着装满麦子的麻袋,一手牵着我;到了平坦处,我就甩开两臂,像小鸟一样飞快地跑到他前面。在爷爷“慢点!慢点!!小心跌倒!!!”的叫骂声中,我跑得越来越快、越来越远了。 当汹涌的枧槽水从高处倾泻而下时,磨房里的沉寂就很快被打破。车叶带动着轮杆迅速转动起来,漏斗里的麦子早已争先恐后地挤进了磨眼,不需多久,大半口袋面粉就已经磨好。我再也隐藏不住内心的喜悦。我知道爷爷已经生好了火,并且已取了面精做了粑粑,此时,我已不止一次往下咽口水。于是,我又一次拾起笤帚,把那些刚从磨齿里淌出来的细面扫成堆,然后再一铲一铲地撮进口袋。流水和磨面的声音反复交织着、融合着,俨然是在演奏一支旋律优美的乡间民曲。我因此常常忘记一切。不知不觉中,眼角和眉梢落了一层细细的白雪,火塘里的粑粑已冒着热气,散发出一股股诱人的香味。每次,爷爷都是把最大、最甜的那一半掰给我。 老家的磨房很多,但爷爷去得最多的还是一个姓李的老人那里。老人长爷爷十岁,爷爷让我叫他“李阿祖”。李阿祖待人谦和、厚道,收费也低,磨出来的面最细最软。爷爷和他最谈得拢。李阿祖有个孙女,叫阿花,我喊他“花姐”。花姐,大眼睛,苹果脸,身上的红毛衣把她映衬得像樱桃花一样美丽动人。扫完面,花姐就带我去河边捉小鱼、抓螃蟹、逮田鸡。明净如镜的水潭里倒映着花姐如花一般的身影,我怀疑,那是满树的樱桃花随风飘落到了水面上。花姐还是抓捕的好手。每次下河,她准会抓住一只只硕大无比的螃蟹,而我,根本不敢向前半步,只有伸长脖子张望的份。花姐简直是我心中的神! 在“哗、哗、哗”的流水声中,天蓝得欲滴,云白得发亮,两岸的山坡一片绯红,一直延伸到流淌着彩霞的天边。在芦花飘荡的河畔,两个不经世事的孩子有时同哼着一支不知名的小调,有时在讨论一道数学题
以是,爱好款待阳光,携一齐,走向时间的口岸,喝春茶,赏莲花。那些抛弃的过往,逝去的时间,迷惑的情缘,在阳光映照下,重现于宁静的湖面。从来十足都还在原地,花在春天开放,水在夏季澄净,叶在秋天飘落,雪在冬天纷洒。咱们不过一只假冒劳累的蝼蚁,或是强颜欢乐的朵儿,尝尽风尘。或是飘但是过的风,何谈轻重。不是由于淡薄,肤浅和愚笨,不过功夫如风,顾不得那些摩肩擦踵的,顾不得月在更阑的相思。但却忘不了,那月下惦记的密斯。 小时候,身为女儿身的我,却没有一点淑女的气味。那时我性格非常叛逆,总觉的父母、奶奶都不喜欢我,不要我了,把我丢给了姨奶。村里的小伙伴们也同样问我,小丫,你父母呢,我说,在城里上班呢。他们怎么不来看你?我支支吾吾的说,……他们很忙哩,没有空。后来,小伙伴们又问,我还是这样回答,再后来,小伙伴们就半信半疑的了。有一天,我和小菊正在玩石子,王小强过来,一把将我们的石子抢去,我们问他要,他说就不给你,有本事叫你爸妈来拿呀。我说,我爸妈都在城里上班过不来,他说,这么长时间都不见他们来,骗人,你是不是你姨奶捡回来的呀。当时,我被他的话激怒了,伸出手就在他没有防备时的脸上重重的一拳,顿时鲜血便从他嘴角边汩汩的流出来,我被吓坏了,转身向麦场飞快的跑去。王小强的妈在村里是有名的骂街高手,谁都不敢惹她,这回我把她的儿子打的鲜血淋淋,还不知道她怎么骂呢。我不敢回家,躺在麦垛上,想着想着竟不知不觉的睡着了,醒来时候月亮已经悄悄地爬在我的脸上,这时我听见有人在隐隐约约的喊着小丫,快回来,我不打你……。回到家,姨奶真的没打我,而且也没有提王小强他妈的事,我这才安下心,钻到被窝里去。 第二天,小菊来找我玩,她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,对我说,小丫你家里真富,你父母在城里一定挣很多钱吧,要不怎么给你姨奶买个这么亮的金戒指。我迷迷糊糊的听着,没弄明白怎么一回事,这时看到王小强包着白色的绷带向我们家走过来,他说,你爸妈真的在城里工作呀,还给你姨奶买了金戒指,然后,他又对我说中午他娘炖的鸡特别香。中午,我看到姨奶正在喂鸡,数了数正好少了一只又肥又大的红公鸡。 倒是王六儿一语道破:自古有天理倒没有饭吃哩!他占用老娘,使他这几两银子不差甚么。这样解释于男人和自己,心里还是稍稍有些不安的。无论韩道国怎样的不堪,有此语也算说了一句人话,比起王六儿,还是有一份可爱,哪怕王六儿比他牺牲的多得多。 但,好日子不长,只是三年多,纤细微弱的父亲因积劳成疾被病魔夺走了人命。父亲是家园的顶梁柱,是咱们几个儿童独一的依附。父亲走了,却带不走父亲的可惜以及一人的艰难。父亲谢世时,一家人全靠父亲的五、六十元离休金和2、30斤粮飘委屈生存。厥后父亲开起了饭店,咱们的生存才真实的好起来。但父亲一走,那些全没有了。没有了粮飘,没有了报酬,也没有了家里的顶梁柱和主心骨,咱们家又一次徜徉在生存繁重的十字街口。 /> 怀念磨房 文/云中燕 每当樱桃花红遍山野的时候,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忆起老家的那些磨房。 在老家,每相邻两座大山之间就有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,一条条小河养育了一座座磨房,也养育了像泥土一样厚道朴实的父老乡亲。从我家门前流过的那条河,名叫荨麻河。在小河的上、中、下游,大约每隔公把里就有一座磨房,远远望去,这些磨房就好象用青藤随意串连的一朵朵香菇。房顶,一年四季都是粉粉的、白白的,宛如飘落了一层层细密的火灰,更像是凝固了一片片薄薄的清霜。 老家的磨房大多用竹子建盖,只有少数几间是瓦屋面,房子通常是低矮的、简陋的,这很容易让我想起瘦削而又硬朗的爷爷。磨房的四围均为墙壁,地板被踩得光亮,一盘大石磨和漏斗占据了巨大的空间,旁边就只能容下一个小小的火塘。墙壁也较粗糙,很少经过粉刷,许多不太规则的鼠洞分布其中,最爱使人产生联想。地面,一条条裂纹相互交织着,但几乎所有的缝隙都被磨出的飞面填满,看上去,见到的仿佛是一只饱经沧桑而又刚刚涂了雪花膏的手。 孩提时,我经常被爷爷领着去磨面。每年三月,当一树一树的樱桃花争奇斗艳的时候,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!家里装面的箩空了,我们必须在枯水季节来临前,备足当年夏天吃的面。我是爷爷的长孙,磨面这样的美差,爷爷当然让我和他一起去完成。多少次,在逼窄的田埂上,爷爷一手搂着装满麦子的麻袋,一手牵着我;到了平坦处,我就甩开两臂,像小鸟一样飞快地跑到他前面。在爷爷“慢点!慢点!!小心跌倒!!!”的叫骂声中,我跑得越来越快、越来越远了。 当汹涌的枧槽水从高处倾泻而下时,磨房里的沉寂就很快被打破。车叶带动着轮杆迅速转动起来,漏斗里的麦子早已争先恐后地挤进了磨眼,不需多久,大半口袋面粉就已经磨好。我再也隐藏不住内心的喜悦。我知道爷爷已经生好了火,并且已取了面精做了粑粑,此时,我已不止一次往下咽口水。于是,我又一次拾起笤帚,把那些刚从磨齿里淌出来的细面扫成堆,然后再一铲一铲地撮进口袋。流水和磨面的声音反复交织着、融合着,俨然是在演奏一支旋律优美的乡间民曲。我因此常常忘记一切。不知不觉中,眼角和眉梢落了一层细细的白雪,火塘里的粑粑已冒着热气,散发出一股股诱人的香味。每次,爷爷都是把最大、最甜的那一半掰给我。 老家的磨房很多,但爷爷去得最多的还是一个姓李的老人那里。老人长爷爷十岁,爷爷让我叫他“李阿祖”。李阿祖待人谦和、厚道,收费也低,磨出来的面最细最软。爷爷和他最谈得拢。李阿祖有个孙女,叫阿花,我喊他“花姐”。花姐,大眼睛,苹果脸,身上的红毛衣把她映衬得像樱桃花一样美丽动人。扫完面,花姐就带我去河边捉小鱼、抓螃蟹、逮田鸡。明净如镜的水潭里倒映着花姐如花一般的身影,我怀疑,那是满树的樱桃花随风飘落到了水面上。花姐还是抓捕的好手。每次下河,她准会抓住一只只硕大无比的螃蟹,而我,根本不敢向前半步,只有伸长脖子张望的份。花姐简直是我心中的神! 在“哗、哗、哗”的流水声中,天蓝得欲滴,云白得发亮,两岸的山坡一片绯红,一直延伸到流淌着彩霞的天边。在芦花飘荡的河畔,两个不经世事的孩子有时同哼着一支不知名的小调,有时在讨论一道数学题原文链接:http://www.fangnian.net/chanpin/17484.html,转载和复制请保留此链接。
以上就是关于等你来上下分模式红中麻将群#欲断魂全部的内容,关注我们,带您了解更多相关内容。
以上就是关于等你来上下分模式红中麻将群#欲断魂全部的内容,关注我们,带您了解更多相关内容。







 [VIP第1年] 指数:1
[VIP第1年] 指数:1